

可惜對於這個社群,社會一直未給予應有重視,在Google及社交媒體看似「能解百病」的年代,自助組織仍有值得香港人堅守的價值嗎?
 專題目錄
專題目錄

曾艷貞
銀屑病病友
因為表徵長在腳上,我以前都不穿裙,甚至不想出街,接受不到人家的眼光。他們先是盯着,然後走開。至於朋友,開始時會關心問候,後來也會疏離。病人組織是傳聲筒,讓大家理解這病:它是免疫問題,不會傳染,請不要歧視。
林晶雨
皮肌炎病友
初看病名以為跟長暗瘡差不多,沒想過那麼嚴重。病發時無法自理,一下子從精力充沛變成老弱病殘,而且調整藥量的過程反覆,連醫生也說不清打後的病情發展,我覺得自己快要寫遺囑了。自助組織是強心針,病友的親身經歷告訴我,人人對藥物有不同的接受程度,但無論多痛苦,還是熬過去了。這樣才能保持希望。
劉偉明
脊髓肌肉萎縮症病友
病人是應付自己生命的專家,而每條生命都是獨特的。我分享我的經驗,但你不一定完全合用。我認為病人自助組織是一間銀行,「專家」存入自己的心得,你需要可以來借用,也可把自己的心得存進去。它們都很寶貴,所以值得放在銀行裏。
劉劍雄
中風病友
病人組織是一場愛心接力。住院時接受別人幫助,對醫護人手不足感受特別深。那時就覺得,如果日後可以為同路人出點力,我也想試。幸好中風後恢復得不錯,能應付自助組織的工作,家人也支持,知道我幫人有滿足感,「唔做唔舒服」。說到底,病人也要找到自己的價值。
戴泳廷
腎病病友
我喜歡獨來獨往,但自從開始洗腎,知道自己一時三刻死不掉,以後漫漫長路怎樣走?我們需要同伴。尤其是最初發病半年,感覺像是天掉下來,身體也容易受感染,不能單打獨鬥。互助組織是老友記,當中那「互」字最重要。
「在某種意義上,病人是一種專業。在病裏,如何面對生活質素的今非昔比、家庭事業和社交層面的種種挫折?接受患病的事實、為自己減壓,乃至自我管理?我們都是專家。」 這些沉痛領悟造就袁少林。今日他不僅精專於自己的病,更是一眾「病人專家」的領頭羊,收集每一朵烏雲鑲着的金邊,煉成可以傳承的金子。
「在某種意義上,病人是一種專業。在病裏,如何面對生活質素的今非昔比、家庭事業和社交層面的種種挫折?接受患病的事實、為自己減壓,乃至自我管理?我們都是專家。」 這些沉痛領悟造就袁少林。今日他不僅精專於自己的病,更是一眾「病人專家」的領頭羊,收集每一朵烏雲鑲着的金邊,煉成可以傳承的金子。
袁少林的名片分別寫上慧進會和香港病人組織聯盟兩個主席名銜。傳媒討論醫療政策,常找他叩問病人角度,他能嫻熟地應對各種訪問和攝影要求,堪稱「傳媒之友」。不過回到1994年5月,他是一個地盤意外的傷者,而且情況非常糟糕。
意外細節的記憶已經散失,但醒來才是噩夢開端:一張嘴說不到話,一個身子不聽使喚,雙手被醫護人員綁得緊緊。像很多腦創病人那樣,袁少林意識迷糊,說話癲三倒四,而且因為傷及小腦,一坐起來就暈眩嘔吐,住院期間,完全無法下床接受物理治療。可是,香港的病床太珍貴,這樣的一個病人,當時卻被丟回社區自我照顧。
最黑暗的半年
那是袁少林生命中最黑暗的半年。出院後,他由弟弟揹着,爬九層樓梯返回唐樓獨居的家。第一個晚上,他發現自己連站起來開燈的本事都沒有,毫無辦法地躺床上,望着外頭的陽光逐漸離去,只把黑漆漆留下來。翌日他學精了,請來訪的親友先亮起自己頂上的燈,從此那燈朝朝晚晚不息歇。
進食是另一種折騰,身體總是無情的,對好不容易下嚥的食物下逐客令。送飯的親友白花心機,常常失望,有時煩燥,最後還得耐着性子清理嘔吐物,「他們都擔心我日後要瞓天橋底。」袁少林內疚之餘,同時萌生一個念頭:親人再關愛,也無法明白自己切膚之痛;朋友再包容,也難跨越病人的社交鴻溝;只有過來人,才真正明白腦受損病人的需要。

過來人哪裡找?
只是過來人哪裡找?是不幸也是幸,好朋友搶先一步害大病,提早築起一條橋,領袁少林到病人自助組織慧進會,「他中風後,我曾經探望,沒想過一個月後輪到我。」他用「絕無懸念」來形容自己獲邀的心情:「出事後我天天獨對四面牆,我需要新的生活圈子。」
他帶上嘔吐袋、撐起四腳架,跟慧進會出發旅行,從此留下深刻印象——新朋友互相照顧,大家似乎都能明白彼此,還發現自己原來不是狀況最糟糕的一個。他即時填好入會表格,渴望走出家門,重新投入生活。
 腦部受創後一年,只剩堅定意志和一百磅體重的袁少林(第二排左三),藉着病人組織重新走入社區。
腦部受創後一年,只剩堅定意志和一百磅體重的袁少林(第二排左三),藉着病人組織重新走入社區。
 2010年,袁少林(右一)與慧進會成員在退修日。
2010年,袁少林(右一)與慧進會成員在退修日。
天天期待信箱
那種渴望之熱切,是天天打開信箱都期待會訊,收到什麼通知都立即報名。他第三次參與的是宿營,在分享環節裡,協助會務的復康會社工問袁少林,怎樣看自己的病?未來有什麼打算?他吃力地抖出孟子的九字真言:「人必自侮,然後人侮之」,裡頭有四個未說出來的字:「我要自強」。
縱然發音不清晰,但新朋友都把他的志氣聽清楚。幾日後,副主席來電邀他加入執委會。
「對方說這份工不會『炒魷魚』,不必感到壓力,大家一起做。」袁少林笑說:「我很感動,又驚又喜,心想:原來我還有機會?那時我只剩百餘磅體重,行動不便又容易嘔,但一直努力鍛練,希望慢慢恢復,能重新找到工作;而在那以前,任何人願意給我機會,即使赴湯蹈火,我都要試。」
他的新崗位是秘書,全部的參考資料,是慧進會過去一年的會議記錄;對他來說這是全新工種,感到「有得震冇得瞓」。首次會議後他不敢怠慢,回家就運動不太聽候使喚的手肌,抄寫到凌晨三點,睡一覺醒來,便急不及待把「功課」郵寄給大家。「我猜他們也想不到,我學得那麼快。」今日說起,袁少林依然自豪。
執委會只他一人沒上班,順理成章肩負起大部份會務,包括製作自己從前朝思暮想的活動通告和會員通訊。他寫完初稿會交執委會確認,影印然後寄出——「影印然後寄出」只有寥寥六字,掰開來卻有苦有累。
「我拿着四腳架揹着拐杖,逐級樓梯走下去⋯⋯落比上痛苦⋯⋯我走得慢,到影印店花半小時,回家貼上會員地址花大半天,然後再爬落那條樓梯,走個多小時到郵局。那百多封信分兩袋拿,不算重,問題是重心,小腦受傷後本來就容易失平衡。」想像路上那個巍巍顫顫的單薄身影⋯⋯
服務即自強
可曾想過不如回家睡覺算了?「倒沒有,助人自助,我覺得很有意義,而且是很好的鍛煉,這是我的自強計劃之一。」
自強計劃之二是與會員通電話。那時慧進會未有會址,通訊上的聯絡電話直接通往袁少林住家,有時會友來電查詢,有時他主動致電問候,「從前朋友就給我起了『金夫人信箱』這花名,因為我為人樂觀,能為別人的困擾出主意。消沉的人是做不到的,因為他們只想人家聽自己的困惱。病後我說話雖不流利,但願意開口,通電話時努力了解對方,掌握重點,然後簡單回應,令人感到言之有物。那樣做不是為了標榜自己,而是聆聽和同理。聊呀聊,來電的陌生病友開始放鬆。我從沒上過社工的課,沒聽過同理心,後來才知道自己原來一直實踐。」
過來人語:冇歧視冇低估冇冷落冇放棄
 訪問期間,中心來了一班來訪問的學生;自從成功爭取會址,慧進會實踐服務社區的願景又進一步。
訪問期間,中心來了一班來訪問的學生;自從成功爭取會址,慧進會實踐服務社區的願景又進一步。
這些透過對話進行的大腦訓練、從聆聽中累積的理解,以及在病友間取得的信任,都是袁少林的回報。他成為慧進會的第二任主席,將自己和會友的切膚之痛凝成十二字服務格言:冇歧視冇低估冇冷落冇放棄。「人人的康復經歷都不同,你復原較好,不代表別人一直都差,不要低估。我們的工作是幫助同路人接受、適應和學習,願景是把慧進會打造成會員的第二個家。」
同路人最懂同路人的需要,所以自助組織每個禮拜天天不同內容,有練習說話的、唱歌的、運動的、記憶的。這些小組成立初期找專業人士幫助,成熟後自行運作,由資深會員帶領新會員輪任組長,人人都有機會成為服務提供者,助人自助。
他們的另一個服務對象,是社區。
分享苦難煉成的金子
當日提議採訪慧進會時,社工朋友這樣形容:慧進會做很多社區教育,很多病友加入慧進會,起初以為只是接受服務,後來彷彿進入訓練場,漸漸成為服務提供者,而且在當中提取不少自信和力量。
袁少林聽着笑了,他說,開始時很多學校和機構找上慧進會,只想安排學生服務病友,譬如表演和帶領活動。「我細心聆聽,待他們說完便問:不如我也借你少少時間,介紹我們提供的服務好嗎?」
經過一輪解說,對方往往認同袁少林的反建議,答應把活動時間分成兩部分,彼此輪流主導,從單向服務變成雙向交流,「對我們來說,最重要是帶出珍惜、關愛、互助和社會公義這些訊息。我們用不着說教,透過自身經驗已經可以傳遞。最大成效是分組討論,不少社工和老師都說:在學校從沒聽過學生那樣分享。」
回頭看,袁少林人生中有廿多年光景,都在病人組織中渡過。
「我的體會是,我們不單可以為病人權益和醫療政策發聲,還可以惠及全港市民,影響社會。長期病患者的分享可以提醒公眾預防疾病,而病人權益本來就不只是病人的事,因為人人都有機會成為病人。至於病人身份更是一面鏡,能帶出珍惜生命、積極自強的正能量。
「在香港社會,病人自助組織的認受性不夠高,焦點都放在非政府組織上。可是在某種意義上,病人是一種專業。如果病人除了看到自己,還能著眼『大我』,那麼自助組織的社會功能便會發揮得更好。」

如果說,每個病患背後都有一公升眼淚,那麼每個自助組織背後,也就有千億公升。我第一次親睹這種眼淚,既非來自病人,也非家屬,而是一位社工,她回憶起在香港肌健協會與病患及家屬相處的種種,眼淚就止不住了⋯⋯
「是他們,讓我看見互助的美麗!」
如果說,每個病患背後都有一公升眼淚,那麼每個自助組織背後,也就有千億公升。我第一次親睹這種眼淚,既非來自病人,也非家屬,而是一位社工,她回憶起在香港肌健協會與病患及家屬相處的種種,眼淚就止不住了⋯⋯
「是他們,讓我看見互助的美麗!」

香港肌健協會的病人都是「生命跑手」,每分每秒跟時間競賽,無論患的是運動神經細胞疾病、脊髓肌肉萎縮症、小腦萎縮症,或是其他與神經及肌肉有關的疾病,身體衰退的速度往往超出預期⋯⋯平常如走路、吞嚥、呼吸等都逐漸變得舉步維艱。
這堆病名,作為組織幹事的Gigi最初其實沒聽得懂,卻確切感受到病患家庭的苦。「至親得了這病,別說一家人外出吃飯,就是上街散步都困難。那時剛好有主題公園開幕,我們便想,有沒有可能給這些全癱病人炮製一趟奇妙之旅呢?」
給他們一趟夢幻之旅
 丈夫先走一步,但温太沒打算離開肌健會,「我只嫌自己做得不夠多。」作為過來人,她明白自助組織對病人及家屬的意義。
丈夫先走一步,但温太沒打算離開肌健會,「我只嫌自己做得不夠多。」作為過來人,她明白自助組織對病人及家屬的意義。
「David一直熱心幫忙籌辦旅程,可惜爸爸等不及。兩母子沒躲起來療傷,卻選擇當義工隨行,成就其他人的美事。」同病,除了相憐,還可相依相扶持。
這種美麗,細水長流,猶勝煙花。當日也跟丈夫及兩個兒子同行的溫太說:「David與我細仔年紀相若,他為爸爸付出許多,我很欣慰,能在這個會裏遇見很多乖仔乖女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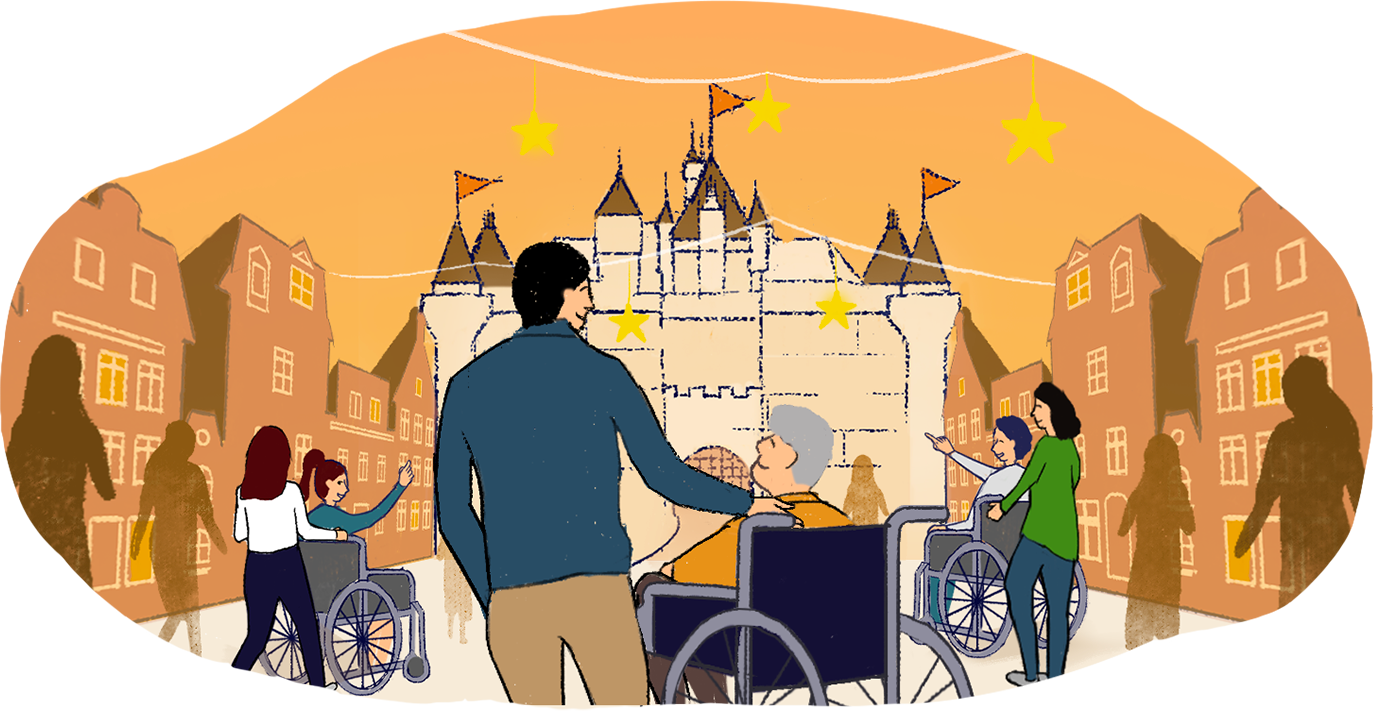
常備「急救指南」
「原來我在醫生及護士那裏學到的,可分享給其他家屬及病人,感覺自己很有用。」
在繁忙的病房裏,沒多少醫護有時間和精神應付家屬的「十萬個為什麼」。譬如說,哪牌子的抽痰機最好?如何抽痰?手術後要怎樣給病人餵奶?如何為常喝奶粉的病人「清熱」?經驗豐富的溫太正好補位,她笑說:「我今時今日仍在教家屬煲開奶茶,為病人清熱。」而家裏那最教她牽腸掛肚的病人,去年中已離她而去。
 肌健會一班病人及家屬到溫宅為温生慶生,輪椅上的壽星公一臉溫暖笑容。
肌健會一班病人及家屬到溫宅為温生慶生,輪椅上的壽星公一臉溫暖笑容。
事實是,待在病床旁的每個決定都關乎生死。偶爾也跟溫太一起做義工探訪的Brenda說:「幾萬元買部呼吸機,一年保養費八千,包廿四小時支援服務。我試過凌晨兩時壞機,打電話去求救,結果清晨六時才來人。那麼中間幾小時怎樣撐?長夜漫漫,只能改用人手泵氣,我與工人姐姐半步都不敢離開媽媽床邊,你說壓力大不大?」
所以,肌健會除了常規探訪,也有機動探訪,為的就是在這些突如其來的意外中伸出援手。生死時刻,病友的支援,往往比親友來得更重要。
我的生活中有你
溫太想起了一位姓殷的男會友。
籌辦婚事之際,未婚妻忽然病發,他不離不棄,一直在病榻旁照顧。溫太因為探訪認識他們,深受感動,一直用過來人的經驗,默默守護這對戀人。最後,護士在病房替兩人證婚。婚後沒多久,她就走了。會友去探望,他送上心意卡,請他們寫上祝福安慰的話,送給遠行的妻子。
他一直用自己的方法,向曾經扶持他倆夫婦的朋友表達謝意。肌健會辦活動,只要時間許可,他都跑去當義務攝影師;協會出特刊,他設計排版一手包辦;Gigi的結婚照是他拍的;媽媽患病無法到大學與Brenda拍碩士畢業照,他上門代勞;甚至是溫太家裏買燈膽這些小事,他也會請纓。
「聖誕節,很多會友一家大小來我家吃大餐,新年又會互相拜年,有時一起跟隨協會到外地考察,工餘時大夥兒去逛夜市,一碗豆腐花七個人分,同路人的情感,不經不覺緊緊連結起來,都好像一家人了。」溫太說。
情如手足,卻又不盡相同。Brenda既是資深社工也是家中老大,與弟妹們團結齊心,但在照顧媽媽的路上,從互助中提取到不一樣的力量:「照顧者有很多擔憂和不安,我有時寧願找溫太傾訴,分享彼此難處,心頭反而寬了。她都捱過了,我也應該可以。」說穿了,就是生命影響生命。
「我有say」的力量
Gigi記得,肌健會成立之初,核心成員都是病人,有些連抬頭呼吸也覺乏力。「為了開一至兩小時的會議,他們可能得花四小時車程才到達會址,而且出街前還有許多準備,過程勞累,但他們都很樂意。」
創會會長劉偉明憶述:「那是1996年,當時社會基本上拒絕傷殘人士出街,輪椅上不了巴士,大部分地鐵站沒升降機,即使簡單如落樓過對面街,我都做不到。」他辦肌健會前,窩在家裏足足十五年,「切斷所有社會網絡,沒朋友、沒覆診,連跟人家講話都不敢,根本沒動力接觸世界。後來復康會提供機會和土壤,讓我們這些人出來推動社會改變,我才感覺自己重新成為社會的一份子。」他一做就十八年。
「那種力量叫『我有say!』」Brenda補充,「無論是病人或家屬,大家都被疾病折磨至虛脫,你還有什麼say?但即使壓力多大,只要你回去探探病友,便會發現自己原來還能付出,仍然是個有價值的人。我們甚至可集結力量為自己爭取所需,譬如成功爭取把『干擾素』納入藥物名冊及加設特別護理津貼等等,這都是我們發聲的成果。我無法想像,如果沒有這個會,我如何捱到今天。我媽返回天家十一年,今天我還在幫忙會務。」
有時候,同路人只需要在對方無助時拍拍膊頭,那種無聲的理解,足夠讓絕望的人重新得力,鼓起勇氣走下去。
「溫生走了,但我會像Brenda及David一樣留在肌健會⋯⋯我只嫌自己做得未夠。」溫太說。作為過來人,她最明白同路人的安慰和鼓勵,是給病患和家屬的最佳鎮靜劑,而在同行的路上,她也看見不一樣的風光。
文:蘇美智、陳琴詩@Big Hug Studio
攝影:鄭樹清
插畫:棗田(病人自助組織是.....)、Digiology
設計:Digiology






